2月5日,我来到江苏省常熟市古里镇紫芙社区,看望90岁的白茆山歌歌手、吴歌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陆瑞英。“快进来,下雨了!”尚未进门,一个爽朗的声音传来,随即,一位体态微胖、满面红光的老太太迎上前来——她就是在常熟四里八乡赫赫有名的山歌“金嗓子”陆瑞英。如久别重逢般,我们自然而然聊起了她唱了一辈子的山歌。

吴歌于2006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典型代表为白茆山歌、芦墟山歌、河阳山歌。江南鱼米之乡有如沃土,一代代山歌手拔节生长,吴歌唱响在田野里、舞台上,并多次走进高校、中南海等“大雅之堂”,为民俗文化研究提供了最鲜活的样本。多方呵护下,有如“天籁自鸣”的吴歌,唱响在新时代的春天里。

来自土地深处的歌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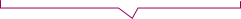
顾颉刚《吴歌小史》中说:“吴歌最早起于何时,我们不甚清楚,但也不会比《诗经》更迟。”
顾颉刚的《吴歌小史》是在整理点校出版冯梦龙的《山歌》基础上完成的。冯梦龙《山歌》收集江南山歌356首,是江南民歌流传的第一功臣。顾颉刚发起民歌研究运动,是冯梦龙之后的又一关键人物。
生在歌乡,从小听祖父辈唱山歌、讲故事,这是山歌手们普遍的成长环境。
陆瑞英从六岁起跟着祖母纺纱织布。纺车转了,祖母的山歌、故事开场了。大鲇鱼相助开通白茆塘、古往今来的英雄好汉——陆瑞英夜夜听祖母唱山歌,肚子里积累了大量山歌和民间故事。

等到陆瑞英13岁的时候,农忙季节,同村的叔叔伯伯带着她去外村打短工。那时候白茆兴“盘工”。陆瑞英解释,就是“今天你帮我做,明天我帮你做”。下田了就开始唱山歌,有人会唱《古人一百零八将》,有人会唱花草的山歌,有人会唱虫豸的山歌,还有的会唱最长的《盘螃蟹》,从一只螃蟹盘到七十二只螃蟹,要盘五六个小时。“唱唱山歌散散心”,唱歌减轻了沉重的体力劳动带来的劳累感,一天的田里生活也就很快过去了。
唱山歌最热闹的场景当属对歌,对歌活动通常在夏秋之际的农闲季节。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泳超的《白茆山歌的现代传承史》一书中提到:“到了对山歌的约定日子,一河两岸人头攒动,河里挤满了船,很多老远的外乡人也闻风而至,白茆塘为之交通壅塞,过往舟船只好停下来,等歌场散后才能继续行进。”“台上台下,岸上水面,你唱我和,尽情高歌。”
陆瑞英家后面,就是昔日热闹的对歌主场——白茆塘。她跟我说,对歌主要是选定歌手和军师。歌手总是挑山歌唱得又好又多的人,军师也是山歌高手,他们未必唱得最好,但一定是肚子里山歌很多,而且有立地编歌的高强本领。等到老歌对光了,这时候军师就派用场了。他们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新编山歌提示歌手,突然掼出来为难对方。

比如,“啥个花开花勿结籽结籽勿开花?啥个花开花就收花?啥个花青枝绿叶勿开到老才开花?啥个花开花结籽再开花?”这些问题不能信口开河瞎回答,文化再高也没有用,要有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对方的军师就要赶紧根据问题找答案,然后编成押韵的歌叫歌手再唱回去。陈泳超说,军师角色是白茆对歌活动中的特殊现象,其他吴语山歌区未曾有过。
本传山歌为后人保存了长篇山歌,张家港的虞永良三十年挖掘、整理、研究河阳山歌,至今收藏了30多本长篇山歌的手抄本,芦墟山歌也保存了20多本手抄长篇山歌,为后人研究吴歌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如目前吴歌中保存最长的《赵圣关还魂》,有6476句。
我在张家港凤凰镇的河阳山歌馆看一只做工精致的小木箱,分上下两层,每一层又有好几格。上层放笔墨纸张,下层放山歌本,还可以放干粮。木箱两边铜环系上绳子,可调可背。这只小木箱在当地叫“小巾箱”。对山歌结束后,不论输赢,接下来就是传歌,相互抄歌。很多长篇山歌也是在这种时候得以传承的。

生活中不光是劳动,还有精神世界的展示部分。中国昆曲古琴学会会长田青说,民歌为什么动人?首先在于感情真挚,非唱不可。胸中有一种感情让你不得不表达,但是语言又有局限,怎么办?“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这是民歌的来源。
吴歌中最具艺术性的是爱情歌曲,历来被研究者关注。其中尤以芦墟山歌收藏的《五姑娘》最为著名,传唱久远。这是一首长篇叙事民歌,讲述了长工徐阿天和地主的妹妹五姑娘的凄美爱情故事。然而在当地,真有不少唱着山歌终成眷属的美满爱情故事。结婚后,他们一起生活、劳作、唱山歌,同时,又把自己钟爱的山歌传给儿孙。千年吴歌,靠着家族间世代传承,生生不息。
多渠道传承焕发生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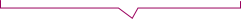
吴歌不光积淀了几千年的优秀传统,同时也在契合时代需求,努力调整自己。白茆山歌学会会长邹养鹤告诉记者,只有跟着时代走,改变一成不变的思路,吴歌才能焕发生命力。
陈泳超认为,苏南城镇化率和农业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原先大规模的、群众性的田间劳作越来越罕见,传统山歌失去了原生态的生存阵地。因此,舞台化将成为白茆山歌等吴歌必然的存在形式。

朝着现代合唱的方向,多地正在创编多声部的新山歌。如:常熟市文化馆的冯艳原创的《舂米歌》,如今成为白茆山歌歌手登台表演的必选曲目;河阳山歌所在的凤凰镇组织专业编剧,先后创作了《嫂娘》《永远的拐杖》《肖家巷里喜事多》等新编河阳山歌剧;吴江区黎里镇文化体育站非遗负责人杨敬伟把《五姑娘》改编成二声部、三声部和五声部,以便适合多种场合的演唱。这些新山歌呈现出立体的表现形式,受到了年轻人的喜爱。
吴歌生存环境的变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如何把握吴歌传承和创新之间的关系,是当地热爱山歌的研究者和长期做山歌田野调查的专家们担忧的问题。
吴歌最好的传承是进校园。十几年来,一大批山歌手走进中小学校园,口口相传这门古老的艺术,其中凤凰还编写了河阳山歌进校园的乡土教材。

专家认为,曲调不能变,变的只能是内容。其次,最能体现各地山歌特色的是方言。但是如今不光是本地的孩子方言说得不太标准,苏南地区学校增加了大量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也让吴歌进校园遇到了难题。第三是唱法,山歌讲究的是原生态发声,强调本嗓演唱,吴歌进校园的授课者,除了本地的知名山歌手,更多的依赖音乐教师。师范专业毕业的音乐教师,多数采用美声唱法。所以,杨敬伟经常“亲自出马”,采用先唱新编山歌激发兴趣,再用传统山歌纠正发声、正本清源,老师在边上一起学习。
高校也是山歌传承和研究的主力。2017年,“乡野天籁——白茆山歌北京高校行”第一站走进北京大学,16位来自白茆山歌艺术团的民歌手,演唱了多首原生态白茆山歌,并与师生交流互动。该活动由陈泳超主持,事实上,陈泳超多年前就到白茆开展田野调查,至今不下二三十次,极大地推进了吴歌在民俗文化领域的研究。
本土高校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十几年来,苏州科技大学、常熟理工学院等高校的音乐系,相继将白茆山歌介入中国民族音乐和中国音乐史的教学中,并邀请山歌手直接进入课堂示范演唱和教学。

吴歌正在实现多渠道传承。早在2004年,常熟理工学院师范学院音乐系副教授王小龙第一次在课堂上开设白茆山歌课程。几年后的一天,他在校园里散步,从车上走下来一位他曾经的学生对他说,“王老师,您以前在课堂上教授白茆山歌,我现在用同样的方法来教授当地的河阳山歌进课堂”。这就是教育的奇妙之处,让王小龙对山歌的前景充满信心。
进入新时代,白茆山歌的现代传承人格局发生了变化。田中、徐洋是常理工音乐系的毕业生,田中擅长音乐制作,徐洋擅长声乐,大学毕业后他们都留在常熟工作,如今已成为白茆山歌艺术团的活跃分子。政府层面的有力推动,以及吴歌自身非常深厚的群众基础,使得老中青三代歌手布局较为均衡。而由于学校教育没有断层,未来也许会涌现出更多年轻的山歌手。
持开放的心态,传统才能出新

王小龙认为,吴歌的传承需两条腿走路,一方面要把优秀的传统保存好、整理好、研究好,才能知道传统的特色在哪里,要继承发扬什么。另一方面,对待创新要持开放的心态。
如何让传统的歌声和当代音乐元素结合起来,从而使传统文化的受众更加广泛?2012年,王小龙做过一个课题,“白茆山歌市场化推进研究”。他的思路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门给民俗音乐推出了一个概念,叫世界音乐,把当今的新潮的配戏加上原生态的歌唱,做成一种现代和原始混生音乐,既能吸引年轻人,同时又有传统元素。王小龙尝试做过几段,虽然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感觉是一种很有益的尝试。

同时他还认为,要尽快让民间原生态文化机制化、机构化。在上海有很多新店开业或者店庆,都会举行声势浩大的锣鼓表演,因此,陕西绛州大鼓在上海生存得非常好,甚至成为了国际化的品牌。如果白茆山歌能够找到合适的切入口,成为准专业的表演团体,能够得到经常性的演出机会,生存和传承问题就能得到部分解决。
依托当地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借助文旅融合生存发展,或是吴歌的一条出路。凤凰镇文化站站长何才荣称凤凰是“最江南”的古镇,河阳山歌馆、永庆寺、凤凰湖为一体的凤凰山景区是国家4A级景区,河阳山歌馆成为游客必到的一个景点。
河阳山歌馆是一处苏式建筑风格的群落,布局精妙,移步易景,且就建在风景优美的凤凰湖畔。整个山歌馆是目前国内展示规模最大的山歌馆,具有展示、演示、学术研究、培训四个功能。截至2020年底,河阳山歌馆参观人数突破50万人次。


每当有游客到来,吴歌省级传承人尹丽芬随即登上小舞台,着古镇水乡服饰,为游客演唱具有代表性的河阳山歌。几位山歌传承人实行轮流值班制,馆里每天都有山歌实景演唱。“这些年,天南海北的人都来听河阳山歌,有的觉得很稀奇,有的十分喜欢,还要了曲谱回去练习。”尹丽芬说。
不光是凤凰,古里镇也将依托古里历史古街区和红豆山庄,探索植入白茆山歌。邹养鹤提出,下一步考虑留出数十亩农田,保留传统的原生态农耕方法,山歌手一边劳作一边唱白茆山歌,更能生动地还原原生态山歌的氛围。“期待各方尤其是青年一代珍惜这项文化遗产,在江南大地上把这动人的歌声一代代传唱下去。”邹养鹤说。
(光明日报全媒体记者 苏雁)









